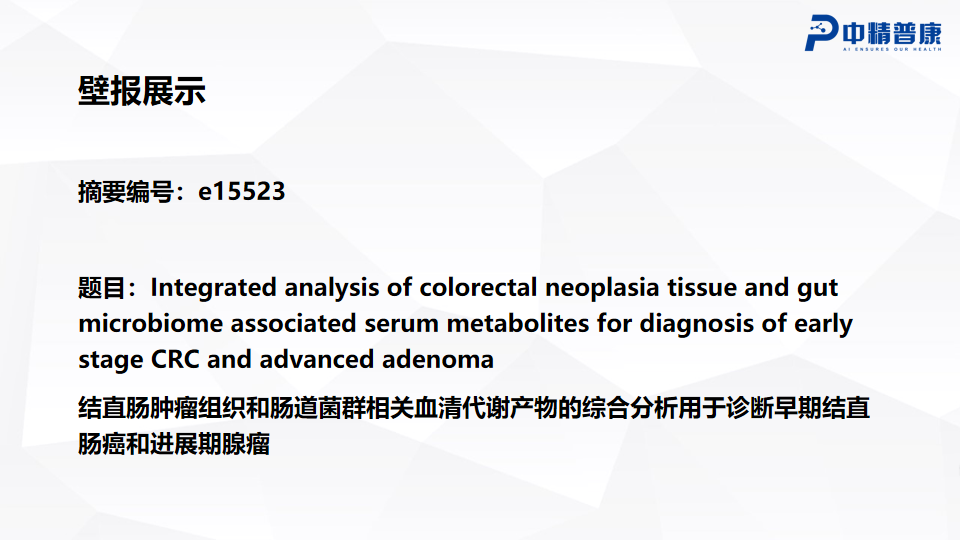世界今亮點(diǎn)!沒人聽也要一直說 嘮叨美學(xué)在誕生
◎趙晨
《咆哮》,一部名字聽起來很像《權(quán)力的游戲》蘭尼斯特族語——聽我怒吼(Hear?me?roar)的Apple自制劇。光看劇名還以為劇集主創(chuàng)們有“要么讓她發(fā)聲,要么聽她咆哮”的烈烈野心和熊熊斗志,然而劇情卻被雄偉的標(biāo)題映襯得出人意料的平淡。
此劇根據(jù)愛爾蘭80后作家Cecelia?Ahern的同名小說改編而來,選取原著中的八篇拍攝,每集30分鐘,短小平淡,頗有小品文之風(fēng)韻,正是貫徹“宇宙之大,蒼蠅之微,皆可取材”之旨。老舍先生曾對(duì)此下過一定義:“小品文,Essay,意思是投擲,像小兒投錢游戲那樣,一下兒便要打著。無論它講說什么,它總須一擊而中,所以它是文藝中的小品,小文章。小,可并不就是容易。”
 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既要輕松又要一擊即中,是對(duì)劇集縱向平衡與深度挖掘的考驗(yàn),《咆哮》選擇從“她”入手。
標(biāo)簽預(yù)告帶來匠氣
首先是視角的高度統(tǒng)一,一至八集均貫徹了片名即主角的原則,她們分別是消失的女人,吃照片的女人,擺在架子上的女人,身上有咬痕的女人,被鴨子喂食的女人,解開自己遇害之謎的女人,退回丈夫的女人和愛馬的女孩。不難看出,這是一次關(guān)于“她”的命題作文,八則故事的主語和關(guān)鍵詞都是“她”。
女性寫作、女性導(dǎo)演、女性主角的三方合力聚焦不同境遇中的她們,不再將她限縮于被凝視的單一境遇中,而是突破男性視角對(duì)女性的想象與限制,從她的經(jīng)驗(yàn)出發(fā),塑造她的形象,講述她的故事,發(fā)出她的聲音,深入挖掘她的內(nèi)心世界。
1975年,勞拉·穆爾維的大作《視覺快感與電影敘事》誕生于女性解放運(yùn)動(dòng)的大潮流中,借助精神分析理論和父權(quán)制秩序兩組資源展開。勞拉指出在主流的電影敘事中包含以男性為中心的“視覺快感”,父權(quán)文化貫穿其中,鏡頭與男性凝視的目光同構(gòu)。論文發(fā)表40年后,NECSUS雜志曾組織女性主義電影研究三人談,再次請(qǐng)回勞拉,結(jié)合自己長期的學(xué)術(shù)經(jīng)驗(yàn)與寫作實(shí)踐,她指出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應(yīng)該放在當(dāng)代而非歷史時(shí)期。此外,當(dāng)下的女性主義不僅在學(xué)術(shù)意義上,還在更廣泛的社會(huì)、文化、政治意義上回歸。循著勞拉的視線觀望《咆哮》,不難發(fā)現(xiàn)這部稍顯平淡的劇集在塑造女性主體、表達(dá)女性困境、構(gòu)建劇集與當(dāng)下的關(guān)聯(lián)、擴(kuò)充女性主義的邊界這幾點(diǎn)上付出了可觀的努力。
除了女性性別這一個(gè)同類項(xiàng),簡單提煉一下八集的關(guān)鍵詞,分別是:族裔、回憶、凝視、平衡、PUA、仇女、物化、復(fù)仇。都是分量不輕的詞匯,而這些重壓詞匯卻環(huán)繞在女性的生活中,以她視角展現(xiàn)這些房間里的大象無疑更為直觀。借助“日常生活”這一在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中被重新發(fā)現(xiàn)并在第三次浪潮中崛起為中堅(jiān)的精神價(jià)值領(lǐng)域來呈現(xiàn)這些困境,力破主義與思想本身無法規(guī)避的形而上氣質(zhì)亦是踴躍嘗試。
但是劇情的硬傷也由此而來,明確的標(biāo)簽使得演員和劇情都囿于完成標(biāo)簽,揭下標(biāo)簽之后人物的立體度和層次性大打折扣,與生活的關(guān)聯(lián)度也稍顯生硬,由是劇情過于直接明晰的現(xiàn)實(shí)指涉顯出三分刻意。劇集中每一個(gè)單集的成功與否,也就取決于如何化解這種由標(biāo)簽預(yù)告所產(chǎn)生的匠氣。
寓言套困境
顯然,這是一部概念大于情節(jié)的劇集。但是這并不令人厭倦,因?yàn)閯〖瘜⑴陨钪兴庥龅陌朔N困窘境遇以寓言的形式呈現(xiàn)出來,從而順理成章地預(yù)演了該境遇的極端狀況,以作警示。寓言是一個(gè)經(jīng)典的詩學(xué)概念,按照柯勒律治的判斷,此概念包含將抽象觀念轉(zhuǎn)化為圖像語言的意義。影視媒介無疑是展現(xiàn)圖像語言的最佳媒介,借助幀幅完成言意同構(gòu),但是,要在三十分鐘內(nèi)將這些抽象的概念、沉重的意義以影像形式展現(xiàn)出來,并且不懸浮,難度系數(shù)頗高。新瓶裝舊酒,寓言套困境,這是《咆哮》的突破路徑與顯著特色。
第一集,黑人女性在公務(wù)會(huì)談中被一幫白人男性忽視,以至于明明在現(xiàn)場(chǎng)的她像是消失了一般,用消失寓言展現(xiàn)被忽視的境遇。
第二集,兒子即將離家,母親患病偶發(fā)失憶,女兒與母親的身份合法性受到雙重挑戰(zhàn),她吃下照片便能找到過去的回憶,由此照片成為回憶的表征。劇集中還提到游戲《塞爾達(dá)傳說》,亦是對(duì)回憶的指涉。
第三集,典型的嬌妻養(yǎng)成記,女性放棄工作嫁人,被困在家庭中的一個(gè)架子上。格奧爾格·西美爾曾在《金錢、性別、現(xiàn)代生活風(fēng)格》一書中如此寫道:“金錢婚姻似乎是一種慢性的賣淫行為,婚姻中金錢操縱的那一部分同等程度內(nèi)在地剝奪了人的——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的——尊嚴(yán)。”被擺放在架子上的女人是被擺放在金錢籌碼上的人,是被剝奪了尊嚴(yán)、被徹底物化進(jìn)而淪為展覽品的人。
第四集,工作家庭難兩全的超人媽媽,難以負(fù)荷的抽象精神重壓以皮膚瘡疤具象展露。
第五集,生活屢屢受挫的單身女性在一只鴨子身上找到了情感依靠,跨物種的愛戀也逃不過異性對(duì)女性的規(guī)訓(xùn)與控制,煤氣燈效應(yīng)在生物界的全方位顯靈。
第六集,以超現(xiàn)實(shí)的手法完成陰陽之我的共同在場(chǎng),揭示男孩因仇女而起殺心的真相,展現(xiàn)生死兩極間的女性困境。
第七集,丈夫成為和衣服鞋子一樣的商品,有標(biāo)價(jià)可退換,與第三集彼此呼應(yīng),物化的兩性寓言。
第八集,探討以女性身份如何面對(duì)復(fù)仇這樁精神倫理事件,同時(shí)以馬揭示女性性別奧秘。
——梳理之后,不難看出劇情并無驚世駭俗的內(nèi)容支撐,也沒有令人目瞪口呆的價(jià)值輸出,有新意但不出挑,有傾向但無立場(chǎng),是一部奉行中庸之道的女性小品文合集,點(diǎn)到即可,過多不談。
在本雅明這里,寓言不僅是修辭學(xué)概念,而且是看待世界的一種方式。在頹敗的現(xiàn)實(shí)境遇面前,寓言的功能在于此間蘊(yùn)含憂郁的碎片、反抗的火種以及威脅的武器。如果從這樣的層面來理解《咆哮》的中庸與平淡,可將其視為平靜的申訴,而不是歇斯底里的呼號(hào)。意圖是讓觀眾看到存在的問題,而不是提出解救之道;目標(biāo)是警示觀眾形勢(shì)嚴(yán)峻,而不是割下異性的頭顱點(diǎn)火歡慶。因而《咆哮》既是獨(dú)像的專注呈現(xiàn),又是群像的眾聲和鳴。將每一集的寓言指涉聚集起來,可以聽到劇方的發(fā)聲:女性依然身處各種各樣的困境,不要忽視。
女性主導(dǎo)自己的表達(dá)
那么平淡和中庸是否意味著《咆哮》不值一提呢?并非如此。當(dāng)代法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大師之一皮埃爾·布爾迪厄認(rèn)為:“‘老生常談’在日常生活中發(fā)揮著巨大的作用,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它,并且是在瞬間接受。”是的,內(nèi)容和題材的平庸恰是“老生常談”的最佳注釋,既然女性的生活中充滿諸多困境,并且未得到改善與幫助,讓更多的人看到,才能談?wù)撓乱徊剑慈绾谓鉀Q。既然有人不聽不看不管不顧,那就不斷地言說,一種嘮叨的美學(xué)在誕生。
近年來,探討女性人格,描摹女性精神的劇集已不少,《使女的故事》《大小謊言》《永不者》都是典例,熒幕上的女性形象日益多元,女性故事圖景逐漸蔚為大觀,隨之浮現(xiàn)的女性問題亦層層堆積在觀眾面前。因此,《咆哮》存在的問題也是整個(gè)社會(huì)文化存在的問題,無路可走的結(jié)局和中庸的表達(dá)不該是我們對(duì)《咆哮》的怨懟,而是對(duì)大環(huán)境的質(zhì)問與懷疑。《咆哮》還不是吶喊,而是上下求索的彷徨,一種溫和的嘗試,不以性別的二元對(duì)立映照女性自身,而是在女性視角下呈現(xiàn)女性經(jīng)驗(yàn),表達(dá)女性境遇,展露女性精神。由此,咆哮也是一種姿態(tài),關(guān)乎探索與交流。寄沉痛于平淡,隱深思于留白,留白處正是你我著墨之地與努力之境。
此外,這并不是妮可·基德曼第一次擔(dān)任制作人,上一次是《大小謊言》,依舊是全女性陣容,依舊探討女性問題,依舊是成績不俗。肉眼可見的是女性精神深度的擴(kuò)展,女性角色人格層次的立體呈現(xiàn),林心如擔(dān)任制作人的《華燈初上》以及賈靜雯擔(dān)任制作人的《媽,別鬧了!》也沿著這一路徑繼續(xù)前進(jìn)。女性主義于這些制作人而言并不只是一個(gè)單薄的口號(hào),而是切實(shí)的生存體驗(yàn)和生命際遇。
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第三季中,萊農(nóng)讓自己的女兒不要看《包法利夫人》,原因是書里到處可以看到男人眼里女人的樣子,女人提出的觀點(diǎn)也被男人當(dāng)成寫作素材。事實(shí)的確如此,女性主導(dǎo)、自己表達(dá),雖然并不一定都是十分佳品,但必然會(huì)為影視世界增添另一種表達(dá)的可能。正如影后弗蘭西斯·麥克多蒙德在2018年奧斯卡頒獎(jiǎng)典禮上的所做所言,她邀請(qǐng)?jiān)趫?chǎng)所有女性的提名者、電影人、制作人、導(dǎo)演、編劇、作曲家等人起立,這個(gè)著名的“罰站”事件讓當(dāng)晚的投資方與制作人進(jìn)一步看到了女性的存在及其身后的力量。最后弗蘭西斯以“Inclusion?Rider”兩個(gè)詞結(jié)束了自己的感言,這指演員在簽署合同時(shí)可加入的一種多元包容條款,以確保電影制作過程中的性別和種族平等。這不僅是影后的感言,也應(yīng)是普通女性的期待。
標(biāo)簽: